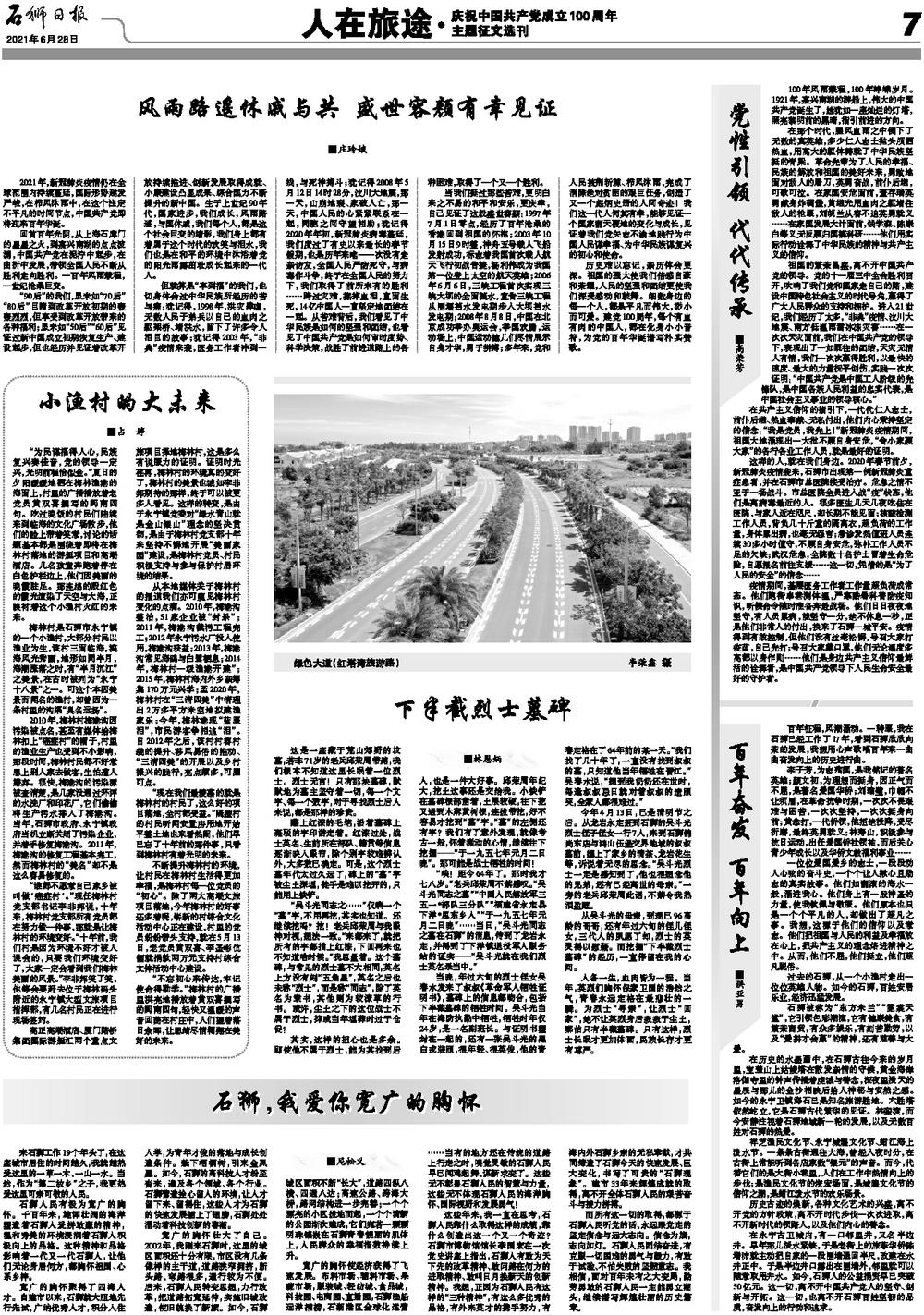这是一座藏于荒山郊野的坟墓,若非71岁的老兵邱荣周带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里长眠着一位烈士。烈士无言!只有那块墓碑,默默地为墓主坚守着一切,每一个文字、每一个数字,对于寻找烈士后人来说,都是那样的珍贵。
蘸上红漆的毛笔,沿着墓碑上斑驳的字印游走着。红漆过处,战士英名、生前所在部队、籍贯等信息逐渐映入眼帘,除个别字较难辨认外,大多数已确定。可是,这个烈士墓年代太过久远了,碑上的“墓”字被尘土深埋,徒手是难以挖开的,只能用上铁铲。
“吴斗光同志之……”仅剩一个“墓”字,不用再挖,其实也知道。还继续挖吗?挖!老兵邱荣周与我眼神对视,想法一致。“来都来了,就把所有的字都描上红漆,下回再来也不知道啥时候。”我思量着。这个墓碑,与常见的烈士墓不大相同,英名上方没有刻“五角星”,英名之后也未称“烈士”,而是称“同志”,除了英名为隶书,其他则为较潦草的行书。或许,尘土之下的这位战士不属于烈士,抑或当年埋葬时过于仓促?
其实,这样的担心也是多余。即使他不属于烈士,能为其找到后人,也是一件大好事。邱荣周年纪大,挖土这事还是交给我。小铁铲在墓碑根部凿着,土层较硬,往下挖又遇到木麻黄树根,连拔带挖,好不容易才挖到“墓”字。“墓”的左侧还有字?我们有了意外发现,就像考古一般,怀着激动的心情,继续往下挖掘——“于一九五七年元月二日晚”。那可能是战士牺牲的时间!
“唉!距今64年了。那时我才七八岁。”老兵邱荣周不禁感叹。“吴斗光同志之墓”“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五一*部队三分队”“福建省永定县下洋*思东乡人”“于一九五七年元月二日晚”……当日,“吴斗光同志之墓在石狮”的消息,传到了龙岩永定,并得到了下洋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的证实——“吴斗光就在我们烈士英名录当中。”
当晚,年过六旬的烈士侄女吴春水发来了叔叔《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墓碑上的信息都吻合,包括下半截墓碑的牺牲时间。吴斗光当年在海防执勤中牺牲,牺牲时年仅24岁,是一名副班长。与证明书塑封在一起的,还有一张吴斗光的黑白戎装照,很年轻、很英俊,他的青春定格在了64年前的某一天。“我们找了几十年了,一直没有找到叔叔的墓,只知道他当年牺牲在晋江。”吴春水说,“想到我奶奶还在世时,每逢叔叔忌日就对着叔叔的遗照哭,全家人都很难过。”
今年4月13日,已是清明节之后。从龙岩永定赶到石狮的吴斗光烈士侄子侄女一行7人,来到石狮锦尚东店与鸿山伍堡交界地域的叔叔墓前,摆上了家乡的清茶、龙岩花生等,诉说着无尽的思念。“吴斗光烈士一定是感知到了,他也很想念他的兄弟,还有已经离世的母亲。”一旁的老兵邱荣周此语,不禁令我热泪盈眶。
从吴斗光的母亲,到现已96高龄的哥哥,还有年过六旬的侄儿侄女,三代人的夙愿了却,烈士的英灵得以慰藉。而挖掘“下半截烈士墓碑”的经历,一直停留在我的心间。
人各一生,血肉皆为一程。当年,英烈们胸怀保家卫国的浩然之气,青春永远定格在最悲壮的一瞬。为烈士“寻亲”,让烈士“回家”,绝不让英烈身后寂寂于尘土,哪怕只有半截墓碑。只有这样,烈士长眠才更加体面,民族长存才更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