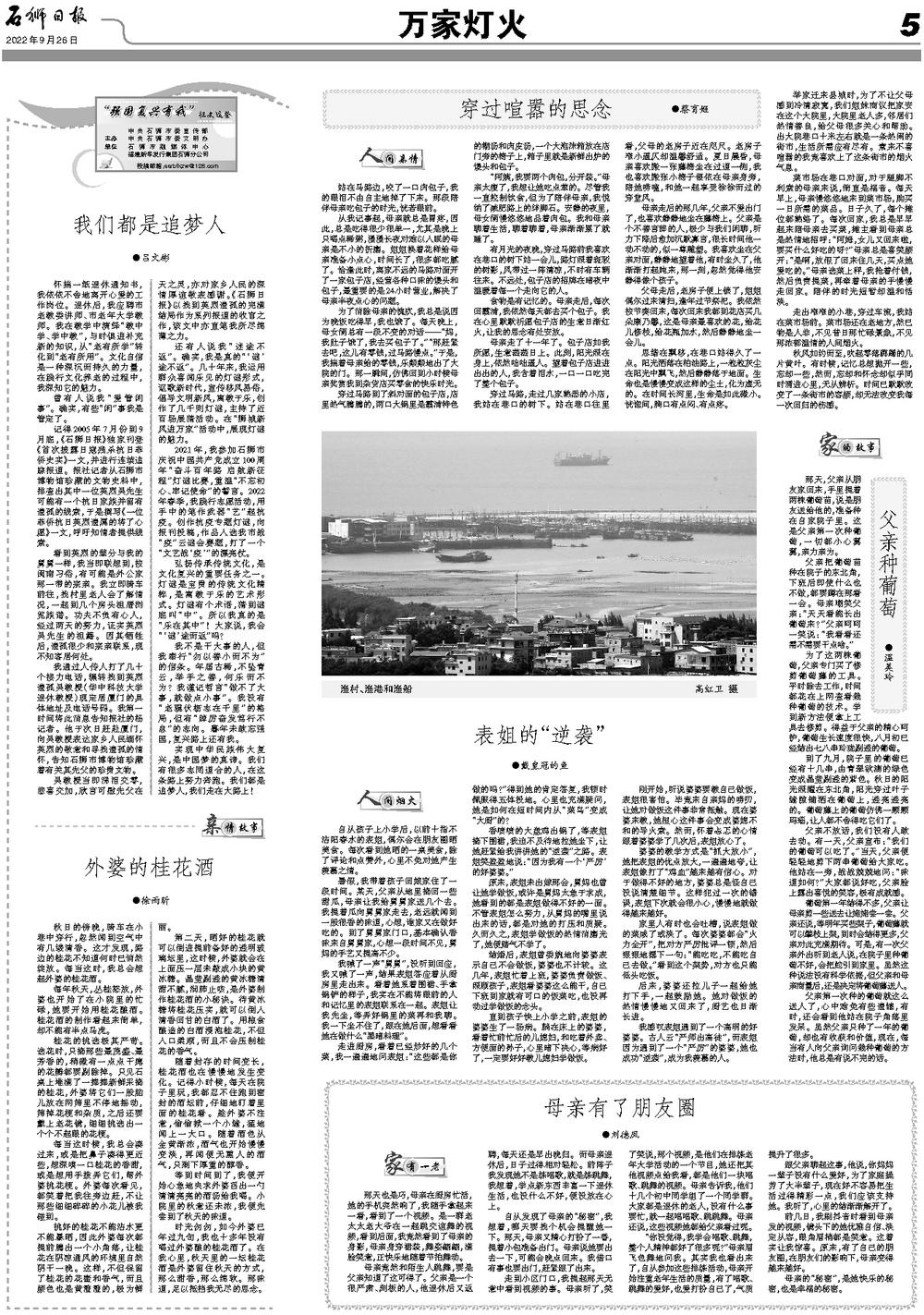站在马路边,咬了一口肉包子,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那段陪伴母亲吃包子的时光,恍若眼前。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总是胃疼,因此,总是吃得很少很单一,尤其是晚上只喝点稀粥,漫漫长夜对难以入眠的母亲是不小的折磨。姐姐换着花样给母亲准备小点心,时间长了,很多都吃腻了。恰逢此时,离家不远的马路对面开了一家包子店,经营各种口味的馒头和包子,最重要的是24小时营业,解决了母亲半夜点心的问题。
为了消除母亲的愧疚,我总是说因为晚饭吃得早,我也饿了。每天晚上,母女俩总有一段不变的对话——“妈,我肚子饿了,我去买包子了。”“那赶紧去吧,这儿有零钱,过马路慢点。”于是,我揣着母亲给的零钱,乐颠颠地出了大院的门。那一瞬间,仿佛回到小时候母亲奖赏我到杂货店买零食的快乐时光。
穿过马路到了斜对面的包子店,店里热气腾腾的,两口大锅里是霞浦特色的糊汤和肉皮汤,一个大泡沫箱放在店门旁的椅子上,箱子里就是新鲜出炉的馒头和包子。
“阿姨,我要两个肉包,分开装。”母亲太瘦了,我想让她吃点荤的。尽管我一直控制饮食,但为了陪伴母亲,我悦纳了减肥路上的绊脚石。安静的夜里,母女俩慢悠悠地品着肉包。我和母亲聊着生活,聊着聊着,母亲渐渐累了就睡了。
有月光的夜晚,穿过马路前我喜欢在巷口的树下站一会儿,路灯照着斑驳的树影,风带过一阵清凉,不时有车辆往来。不远处,包子店的招牌在暗夜中温暖着每一个走向它的人。
食物是有记忆的。母亲走后,每次回霞浦,我依然每天都去买个包子。我在心里默默祈愿包子店的生意日渐红火,让我的思念有处安放。
母亲走了十一年了。包子店如我所愿,生意蒸蒸日上。此刻,阳光照在身上,依然咄咄逼人。望着包子店进进出出的人,我含着泪水,一口一口吃完了整个包子。
穿过马路,走过几家熟悉的小店,我站在巷口的树下。站在巷口往里看,父母的老房子近在咫尺。老房子窄小逼仄却温馨舒适。夏日晨昏,母亲喜欢搬一张藤椅坐在过道一侧,我也喜欢搬张小椅子偎依在母亲身旁,陪她唠嗑,和她一起享受徐徐而过的穿堂风。
母亲走后的那几年,父亲不爱出门了,也喜欢静静地坐在藤椅上。父亲是个不善言辞的人,极少与我们闲聊,听力下降后愈加沉默寡言,很长时间他一动不动的,似一尊雕塑。我喜欢坐在父亲对面,静静地望着他,有时坐久了,他渐渐打起盹来,那一刻,忽然觉得他安静得像个孩子。
父母走后,老房子便上锁了,姐姐偶尔过来清扫,逢年过节祭祀。我依然按节奏回来,每次回来我都到花店买几朵康乃馨,这是母亲最喜欢的花,给花儿修枝,给花瓶加水,然后静静地坐一会儿。
思绪在飘移,在巷口站得久了一点。阳光洒落在柏油路上,一粒粒灰尘在阳光中飘飞,然后静静落于地面。生命也是慢慢变成这样的尘土,化为虚无的。在时间长河里,生命是如此微小。恍惚间,胸口有点闷、有点疼。
举家迁来县城时,为了不让父母感到冷清寂寞,我们姐妹商议把家安在这个大院里,大院里老人多,邻居们热情善良,给父母很多关心和帮助。出大院巷口十米左右就是一条热闹的街市,生活所需应有尽有。素来不喜喧嚣的我竟喜欢上了这条街市的烟火气息。
菜市场在巷口对面,对于腿脚不利索的母亲来说,简直是福音。每天早上,母亲慢悠悠地来到菜市场,购买一日所需的菜品。日子久了,每个摊位都熟络了。每次回家,我总是早早起来陪母亲去买菜,摊主看到母亲总是热情地招呼:“阿姆,女儿又回来啦,要买什么好吃的呀?”母亲总是喜笑颜开:“是啊,放假了回来住几天,买点她爱吃的。”母亲选菜上秤,我抢着付钱,然后负责提菜,再牵着母亲的手慢慢走回家。陪伴的时光短暂却温和恬淡。
走出窄窄的小巷,穿过车流,我站在菜市场前。菜市场还在老地方,然已物是人非,不见昔日那忙碌景象,不见那浓郁温情的人间烟火。
秋风如约而至,吹起零落踯躅的几片黄叶。有时候,记忆总想抛开一些,忘却一些,然而,忘却和怀念却似乎同时涌进心里,无从辨析。时间已默默改变了一条街市的容颜,却无法改变我每一次回归的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