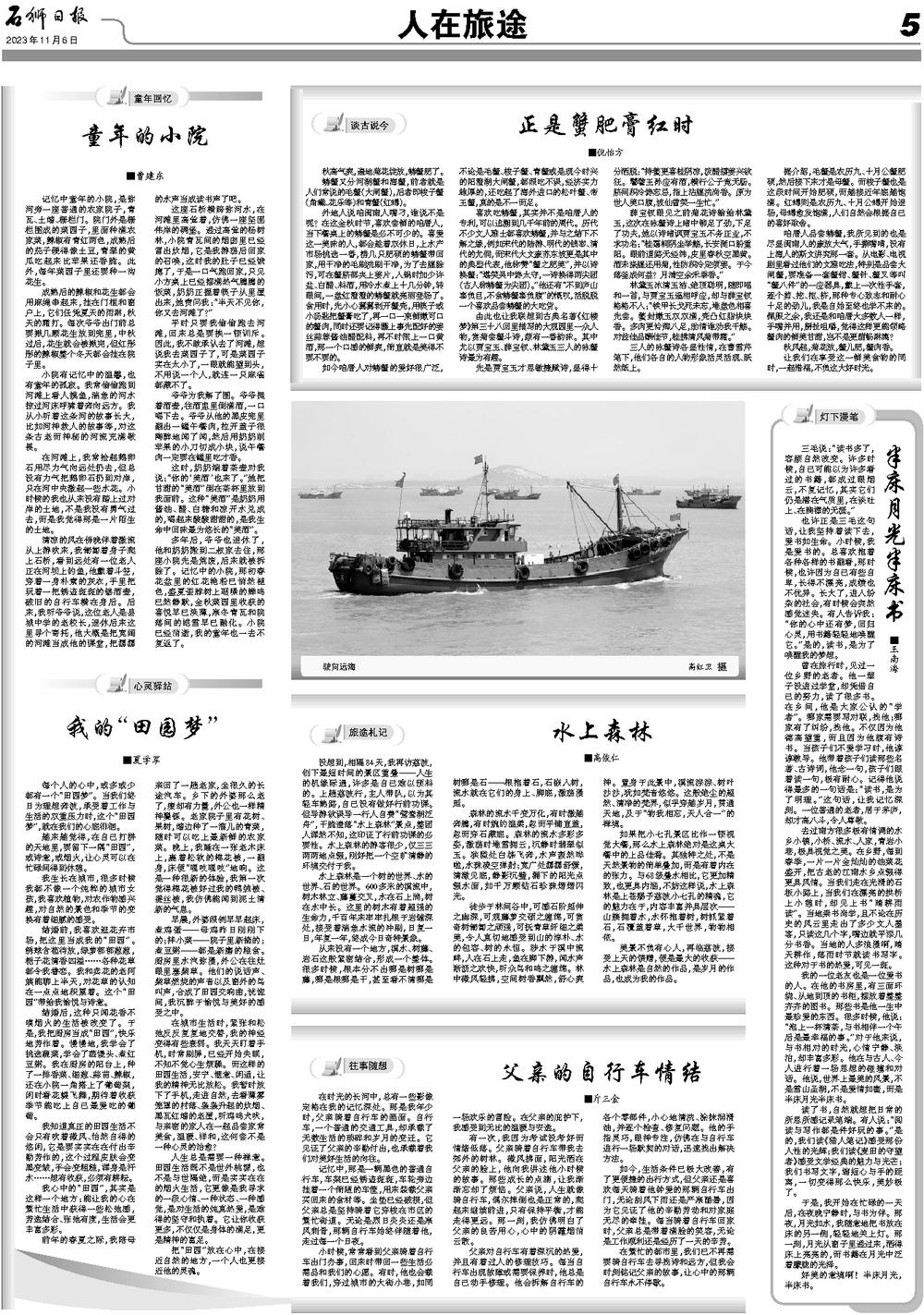秋高气爽,遍地菊花绽放,螃蟹肥了。
螃蟹又分河湖蟹和海蟹,前者就是人们常说的毛蟹(大闸蟹),后者即梭子蟹(角蠘、花乐等)和青蟹(红蟳)。
外地人说咱闽南人嘴刁,谁说不是呢?在这金秋时节,喜欢尝鲜的咱厝人,当下餐桌上的螃蟹是必不可少的。喜爱这一美味的人,都会趁着双休日,上水产市场挑选一番,捞几只肥硕的螃蟹带回家,用干净的毛刷洗刷干净,为了去腥除污,可在蟹脐部夹上姜片,入锅时加少许盐、白醋、料酒,用冷水煮上十几分钟,转眼间,一盘红澄澄的螃蟹就亮丽登场了。食用时,先小心翼翼剥开蟹壳,用筷子或小汤匙把蟹膏吃了,再一口一束鲜嫩可口的蟹肉,同时还要记得蘸上事先配好的姜丝蒜蓉酱油醋配料,再不时抿上一口黄酒,那一个口感的鲜爽,简直就是美得不要不要的。
如今咱厝人对螃蟹的爱好很广泛,不论是毛蟹、梭子蟹、青蟹或是现今时兴的阳澄湖大闸蟹,都照吃不误,经济实力雄厚的,还吃起了海外进口的松叶蟹、帝王蟹,真的是不一而足。
喜欢吃螃蟹,其实并不是咱厝人的专利,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周代。历代不少文人雅士都喜欢螃蟹,并与之结下不解之缘,例如宋代的陆游、明代的钱宰、清代的尤侗,而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称赞“蟹之肥美”,并以诗换蟹:“堪笑吴中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古人称螃蟹为尖团)。”他还有“不到庐山辜负目,不食螃蟹辜负腹”的慨叹,活脱脱一个喜欢品尝螃蟹的大吃货。
由此也让我联想到古典名著《红楼梦》第三十八回里描写的大观园里一众人物,赏菊尝蟹斗诗,颇有一番韵味。其中尤以贾宝玉、薛宝钗、林黛玉三人的咏蟹诗最为有趣。
先是贾宝玉才思敏捷赋诗,显得十分洒脱:“持螯更喜桂阴凉,泼醋擂姜兴欲狂。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竟无肠。脐间积冷馋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原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薛宝钗眼见之前菊花诗输给林黛玉,这次在咏蟹诗上暗中铆足了劲,下足了功夫,她以诗暗讽贾宝玉不务正业,不求功名:“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酒未涤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
林黛玉冰清玉洁、绝顶聪明,随即唱和一首,与贾宝玉遥相呼应,却与薛宝钗格格不入:“铁甲长戈死未忘,堆盘色相喜先尝。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多肉更怜卿八足,助情谁劝我千觞。对兹佳品酬佳节,桂拂清风菊带霜。”
三人的咏蟹诗各显性情,在曹雪芹笔下,他们各自的人物形象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据介绍,毛蟹是农历九、十月公蟹肥硕,然后接下来才是母蟹。而梭子蟹也是这段时间开始肥硕,而越接近年底越饱满。红蟳则是农历九、十月公蟳开始退场,母蟳愈发饱满,人们自然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取舍。
咱厝人品尝螃蟹,我所见到的也是尽显闽南人的豪放大气,手撕嘴啃,没有上海人的斯文讲究那一套。从电影、电视剧里看过他们的文雅吃法,特别是品尝大闸蟹,要准备一套蟹钳、蟹针、蟹叉等叫“蟹八件”的一应器具,戴上一次性手套,逐个剪、挖、抠、挤,那种专心致志和耐心十足的劲儿,我是自始至终也学不来的。佩服之余,我还是和咱厝大多数人一样,手嘴并用,掰扯咀嚼,觉得这样更能领略蟹肉的鲜美甘甜,岂不是更酣畅淋漓?
秋风起,菊花放,蟹儿肥,蟹肉香。
让我们在享受这一鲜美食物的同时,一起惜福,不负这大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