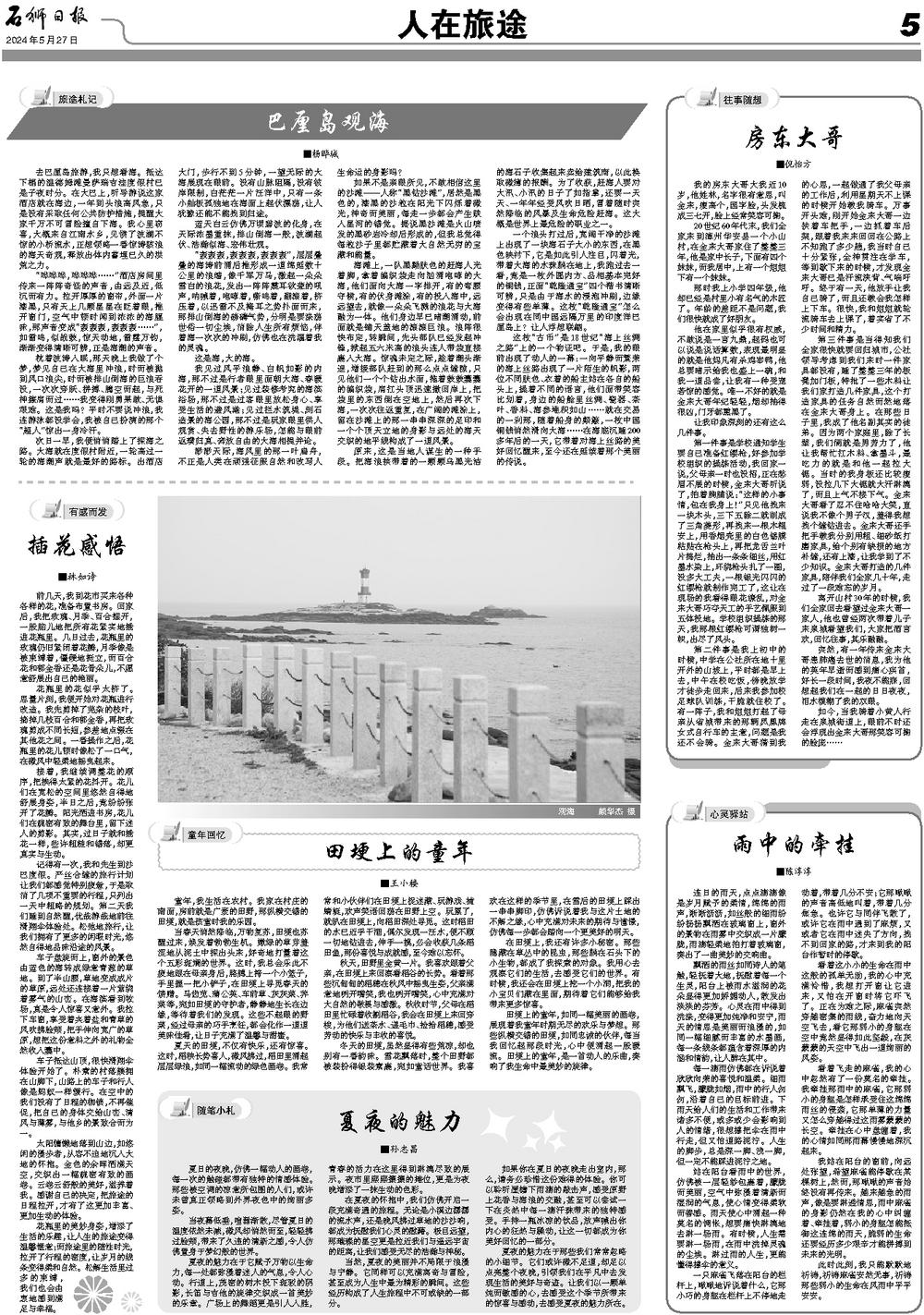■杨晔城
去巴厘岛旅游,我只想看海。抵达下榻的温德姆滩曼萨瑞吉洼度假村已是子夜时分。在大巴上,听导游说这家酒店就在海边,一年到头浪高风急,只是没有采取任何公共防护措施,提醒大家千万不可冒险擅自下海。我心里窃喜,大概来自江南水乡,见惯了波澜不惊的小桥流水,正想领略一番惊涛骇浪的海天奇观,释放出体内蓄埋已久的洪荒之力。
“哗哗哗,哗哗哗……”酒店房间里传来一阵阵奇怪的声音,由远及近,低沉而有力。拉开厚厚的窗帘,外面一片漆黑,只有天上几颗星星在眨着眼,推开窗门,空气中顿时闻到浓浓的海腥味,那声音变成“轰轰轰,轰轰轰……”,如雷鸣,似战鼓,惊天动地,雷霆万钧,渐渐变得清晰可辨,正是海潮的声音。
枕着波涛入眠,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大海里冲浪,时而被抛到风口浪尖,时而被排山倒海的巨浪吞没,一次次穿跃、拼搏、腾空而起,与死神擦肩而过……我变得刚勇果敢、无惧艰难。这是我吗?平时不要说冲浪,我连游泳都没学会,我被自己扮演的那个“超人”惊出一身冷汗。
次日一早,我便悄悄踏上了探海之路。大海就在度假村附近,一轮高过一轮的海潮声就是最好的路标。出酒店大门,步行不到5分钟,一望无际的大海展现在眼前。没有山脉阻隔,没有彼岸限制,白茫茫一片汪洋中,只有一条小舢板孤独地在海面上起伏漂荡,让人犹豫还能不能找到归途。
蓝天白云仿佛万顷碧波的化身,在天际浓墨重抹,排山倒海一般,波澜起伏、浩瀚似海、宏伟壮观。
“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层层叠叠的海涛前涌后推形成一道绵延数十公里的浪墙,像千军万马,激起一朵朵雪白的浪花,发出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吼声,呐喊着,咆哮着,嘶鸣着,翻滚着,挤压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面而来,那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分明是要涤荡世俗一切尘埃,消除人生所有烦恼,伴着海一次次的冲刷,仿佛也在洗濯着我的灵魂。
这是海,大的海。
我见过风平浪静、白帆如影的内海,那不过是行者眼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一道风景;见过装修考究的海滨浴场,那不过是过客眼里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避风港;见过拦水筑堤、刻石造景的海公园,那不过是玩家眼里供人观赏、失去野性的游乐场,怎能与眼前返璞归真、奔放自由的大海相提并论。
渺渺天际,海风里的那一叶扁舟,不正是人类在顽强征服自然和改写人生命运的身影吗?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不敢相信这里的沙滩——人称“黑钻沙滩”,居然是黑色的,漆黑的沙粒在阳光下闪烁着微光,神奇而美丽,每走一步都会产生跌入星河的错觉。据说黑沙滩是火山喷发的黑砂岩冷却后形成的,但我总觉得每粒沙子里都贮藏着大自然无穷的宝藏和能量。
海滩上,一队黑黝肤色的赶海人光着脚,拿着编织袋走向汹涌咆哮的大海,他们面向大海一字排开,有的弯腰守候,有的伏身滩涂,有的投入海中,远远望去,就像一朵朵飞溅的浪花与大海融为一体。他们身边早已暗潮涌动,前面就是铺天盖地的滚滚巨浪。浪阵很快布定,转瞬间,先头部队已经发起冲锋,掀起五六米高的浪头连人带袋直接裹入大海。惊魂未定之际,趁着潮头渐退,增援部队赶到的那么点点缝隙,只见他们一个个钻出水面,拖着鼓鼓囊囊的编织袋,肩扛头顶迅速撤回岸上,把袋里的东西倒在空地上,然后再次下海,一次次往返重复,在广阔的滩涂上,留在沙滩上的那一串串深深的足印和一个个顶天立地的身影与远处的海天交织的地平线构成了一道风景。
原来,这是当地人谋生的一种手段。把海浪挟带着的一颗颗乌黑光洁的海石子收集起来卖给建筑商,以此换取微簿的报酬。为了收获,赶海人要对大汛、小汛的日子了如指掌,还要一天天、一年年经受风吹日晒,冒着随时突然降临的风暴及生命危险赶海。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
一个浪头打过后,宽阔干净的沙滩上出现了一块海石子大小的东西,在黑色映衬下,它是如此引人注目,闪着光,带着大海的水珠躺在地上,我跑过去一看,竟是一枚外圆内方、品相基本完好的铜钱,正面“乾隆通宝”四个楷书清晰可辨,只是由于海水的浸泡冲刷,边缘变得有些单薄。这枚“乾隆通宝”怎么会出现在同中国远隔万里的印度洋巴厘岛上?让人浮想联翩。
这枚“古币”是18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物证吧。于是,我的眼前出现了动人的一幕:一向平静而繁荣的海上丝路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帆影,两位不同肤色、衣着的船主站在各自的船头上,操着不同的语言,他们面带笑容比划着,身边的船舱里丝绸、瓷器、茶叶、香料、海参堆积如山……就在交易的一刹那,随着船身的颠簸,一枚中国铜钱悄然滑向大海……在海底沉睡200多年后的一天,它带着对海上丝路的美好回忆醒来,至今还在延续着那个美丽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