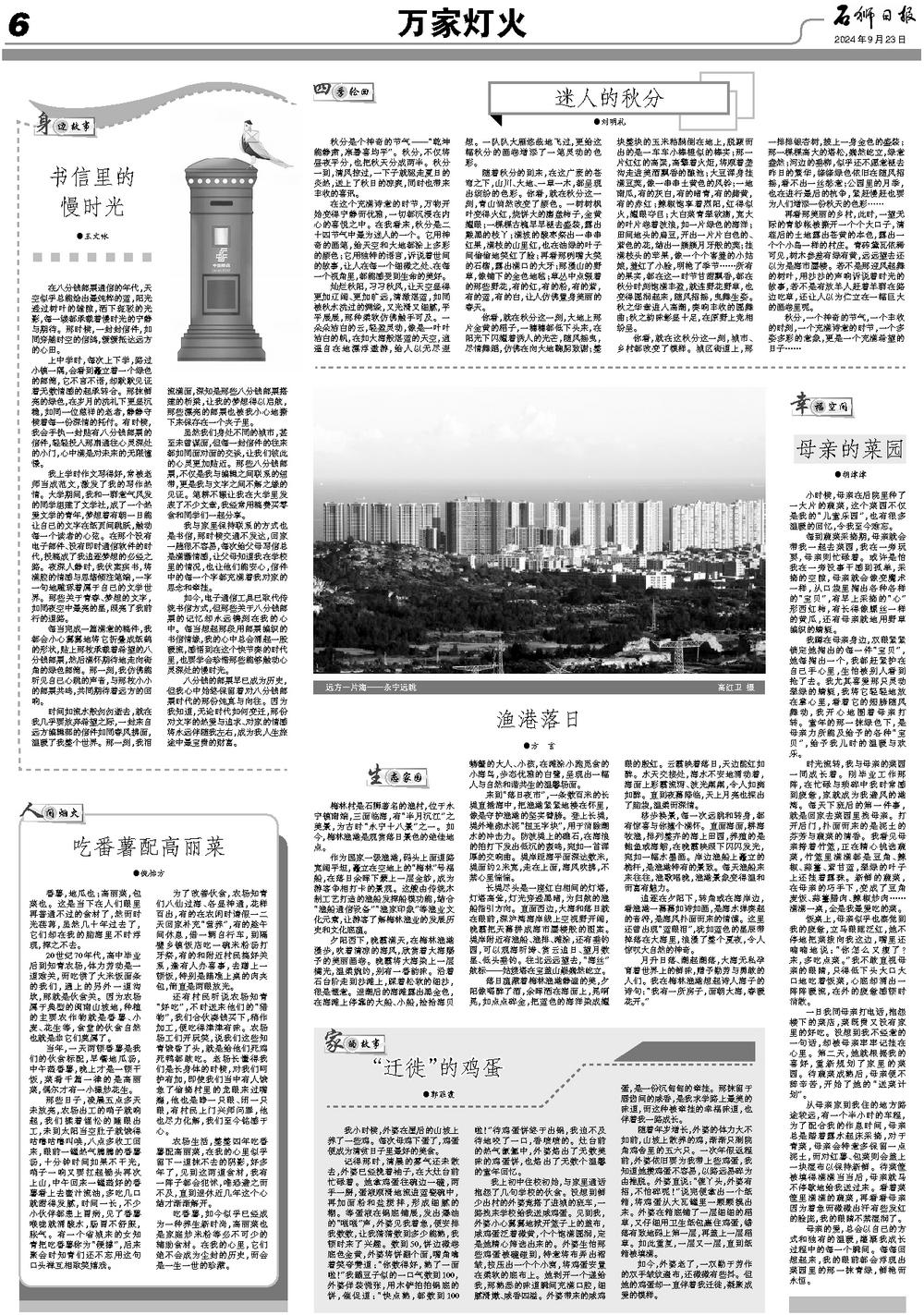●倪怡方
番薯,地瓜也;高丽菜,包菜也。这是当下在人们眼里再普通不过的食材了,然而时光荏苒,虽然几十年过去了,它们却在我的脑海里不时浮现,挥之不去。
20世纪70年代,高中毕业后到知青农场,体力劳动是一道难关,而吃惯了大米饭面条的我们,遇上的另外一道沟坎,那就是伙食关。因为农场属于典型的闽南山坡地,种植的主要农作物就是番薯、小麦、花生等,食堂的伙食自然也就是非它们莫属了。
当年,一天两顿番薯是我们的伙食标配,早餐地瓜汤,中午蒸番薯,晚上才是一顿干饭,菜肴千篇一律的是高丽菜,偶尔才有一小撮炒花生。
那些日子,凌晨五点多天未放亮,农场出工的哨子就响起,我们揉着惺忪的睡眼出工,未到太阳当空肚子就饿得咕噜咕噜叫唤,八点多收工回来,眼前一罐热气腾腾的番薯汤,十分钟时间如果不干光,哨子一响又要扛起锄头再次上山,中午回来一罐蒸好的番薯看上去蜜汁流油,多吃几口就甜得发腻,时间一长,不少小伙伴都患上胃病,见了番薯喉咙就涌酸水,肠胃不舒服,胀气。有一个省城来的女知青把吃番薯称为“硬撑”,后来聚会时知青们还不忘用这句口头禅互相取笑嬉戏。
为了改善伙食,农场知青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花样百出,有的在农闲时请假一二天回家补充“营养”,有的趁午间休息,借一辆自行车,到隔壁乡镇饭店吃一碗米粉汤打牙祭,有的和附近村民搞好关系,逢有人办喜事,去蹭上一顿饭,特别是瞄准上桌的肉夹包,简直是两眼放光。
还有村民听说农场知青“好吃”,不时送来他们的“猎物”,我们合伙凑钱买下,稍作加工,便吃得津津有味。农场场工们开玩笑,说我们这些知青饿昏了头,就是给他们死鸡死鸭都敢吃。老场长懂得我们是长身体的时候,对我们呵护有加,即使我们当中有人饿急了偷摘村里的龙眼来过嘴瘾,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村民上门兴师问罪,他也尽力化解,我们至今铭感于心。
农场生活,整整四年吃番薯配高丽菜,在我的心里似乎留下一道抹不去的阴影,好多年了,见到这两道食材,我有一阵子都会犯怵,唯恐避之而不及,直到退休近几年这个心结才渐渐解开。
吃番薯,如今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养生新时尚,高丽菜也是家庭炒米粉等必不可少的辅助食材。在我的心里,它们绝不会成为尘封的历史,而会是一生一世的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