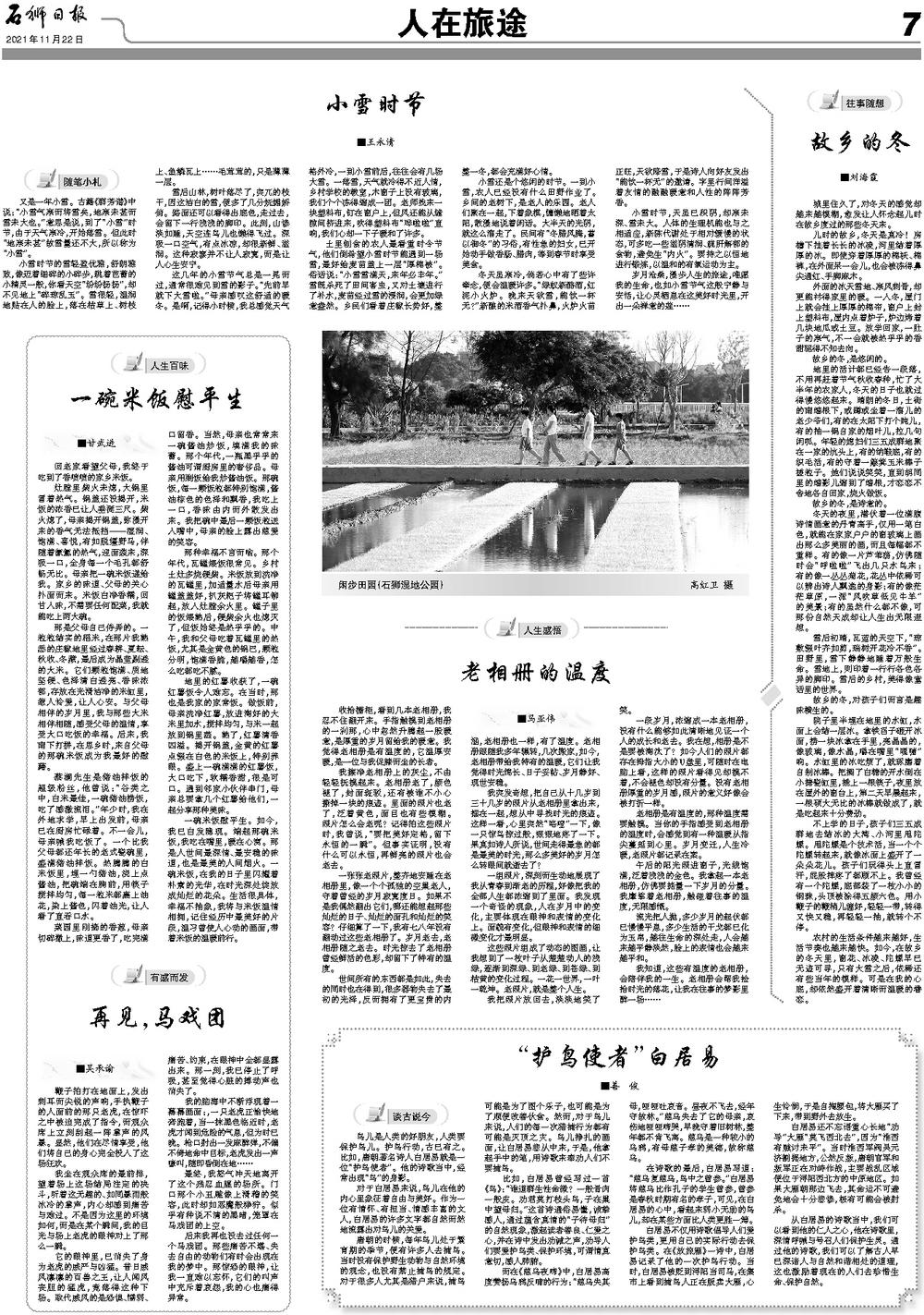回老家看望父母,我终于吃到了香喷喷的家乡米饭。
灶膛里柴火未熄,大锅里冒着热气。锅盖还没揭开,米饭的浓香已让人垂涎三尺。柴火熄了,母亲揭开锅盖,弥漫开来的香气无法抵挡——湿润、饱满、喜悦,有如脱缰野马,伴随着氤氲的热气,迎面袭来,深吸一口,全身每一个毛孔都舒畅无比。母亲把一碗米饭递给我。家乡的味道、父母的关心扑面而来。米饭白净香糯,回甘入味,不需要任何配菜,我就能吃上两大碗。
那是父母自己侍弄的。一粒粒结实的稻米,在那片我熟悉的庄稼地里经过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最后成为晶莹剔透的大米。它们颗粒饱满、质地坚硬、色泽清白透亮、香味浓郁,存放在光滑洁净的米缸里,惹人怜爱,让人心安。与父母相伴的岁月里,我与那些大米相伴相随,感受父母的温情,享受大口吃饭的幸福。后来,我南下打拼,在思乡时,来自父母的那碗米饭成为我最好的慰藉。
蔡澜先生是猪油拌饭的超级粉丝,他曾说:“谷类之中,白米最佳,一碗猪油捞饭,吃了感激流泪。”年少时,我在外地求学,早上出发前,母亲已在厨房忙碌着。不一会儿,母亲喊我吃饭了。一个比我父母都还年长的老式瓷碗里,盛满猪油拌饭。热腾腾的白米饭里,埋一勺猪油,浇上点酱油,把碗端在胸前,用筷子搅拌均匀,每一粒米都裹上油花,染上酱色,闪着油光,让人看了直吞口水。
菜园里刚摘的香葱,母亲切碎撒上,味道更香了,吃完满口留香。当然,母亲也常常来一碗酱油炒饭,填满我的味蕾。那个年代,一瓶黑乎乎的酱油可谓厨房里的奢侈品。母亲用剩饭给我炒酱油饭。那碗饭,每一颗饭粒都特别饱满,酱油棕色的色泽和飘香,我吃上一口,香味由内而外散发出来。我把碗中最后一颗饭粒送入嘴中,母亲的脸上露出慈爱的笑容。
那种幸福不言而喻。那个年代,瓦罐煨饭很常见。乡村土灶多烧硬柴。米饭放到洗净的瓦罐里,加适量水后母亲用罐盖盖好,扒灰耙子将罐耳铆起,放入灶膛余火里。罐子里的饭煨熟后,硬柴余火也熄灭了,但饭始终是热乎乎的。中午,我和父母吃着瓦罐里的热饭,尤其是金黄色的锅巴,颗粒分明,饱满香脆,越嚼越香,怎么吃都吃不腻。
地里的红薯收获了,一碗红薯饭令人难忘。在当时,那也是我家的家常饭。做饭前,母亲洗净红薯,放进淘好的大米里加水,搅拌均匀,与米一起放到锅里蒸。熟了,红薯清香四溢。揭开锅盖,金黄的红薯点缀在白色的米饭上,特别养眼。盛上一碗满满的红薯饭,大口吃下,软糯香甜,很是可口。遇到邻家小伙伴串门,母亲总要拿几个红薯给他们,一起分享那种美味。
一碗米饭慰平生。如今,我已白发隐现。端起那碗米饭,我吃在嘴里,暖在心窝。那是人世间最深情、最安稳的味道,也是最美的人间烟火。一碗米饭,在我的日子里闪耀着朴素的光华,在时光深处绽放成灿烂的花朵。生活很具体,幸福不抽象,我将与米饭温情相拥,记住经历中最美好的片段,温习曾使人心动的画面,带着米饭的温暖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