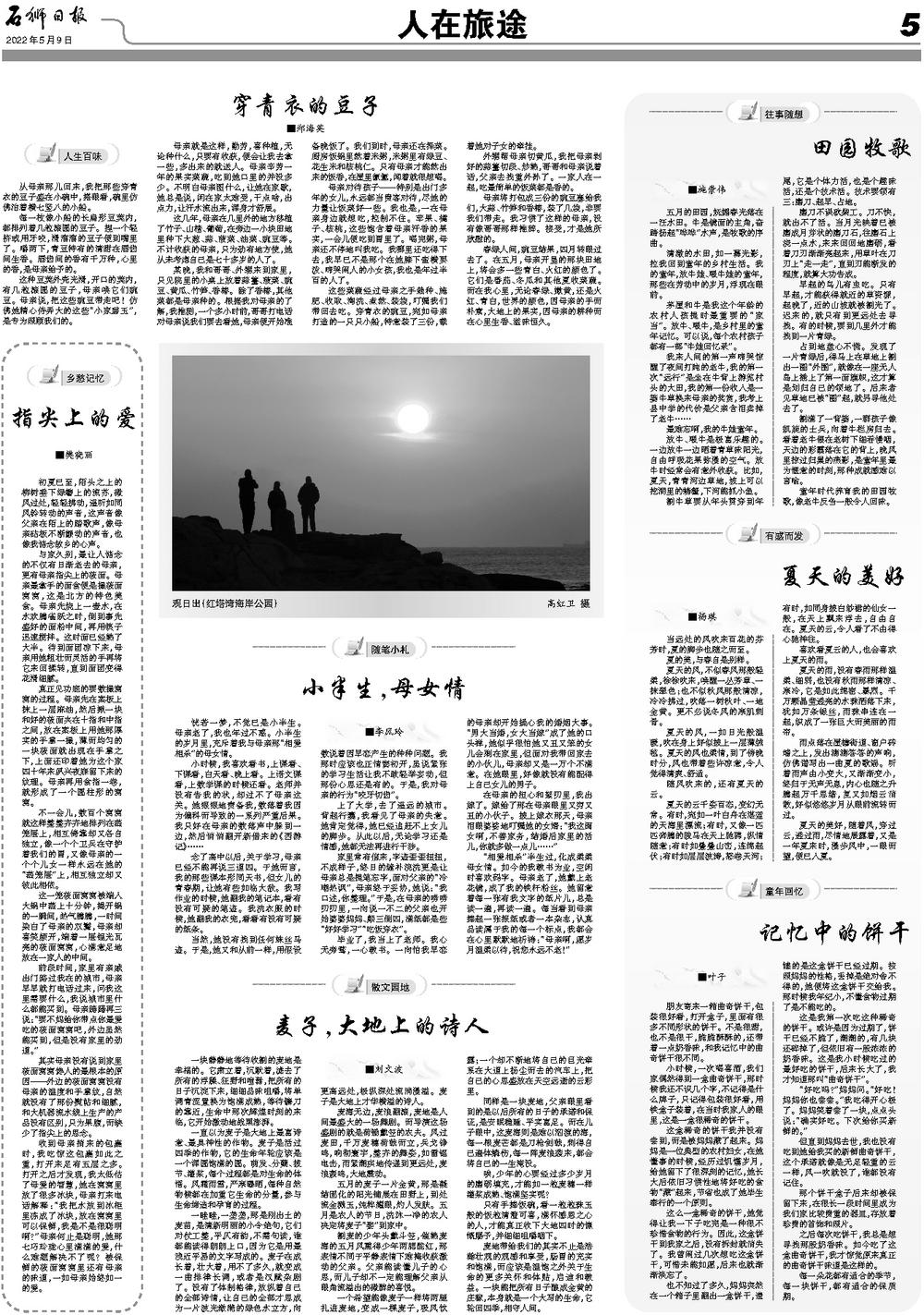五月的田园,妩媚春光落在一汪水田。牛是镜面的主角,奋蹄扬起“哗哗”水声,是牧歌的序曲。
清澈的水田,如一幕光影,拉我回到童年的乡村生活。我的童年,放牛娃、喂牛娃的童年,那些在劳动中的岁月,浮现在眼前。
茅屋和牛是我这个年龄的农村人孩提时最重要的“家当”。放牛、喂牛,是乡村里的童年记忆。可以说,每个农村孩子都有一部“牛娃回忆录”。
我来人间的第一声啼哭惊醒了夜间打盹的老牛,我的第一次“远行”是坐在牛背上游览村头的大田,我的第一份收入是一篓牛草换来母亲的奖赏,我考上县中学的代价是父亲含泪卖掉了老牛……
最难忘啊,我的牛娃童年。
放牛、喂牛是极富乐趣的。一边放牛一边晒着青草味阳光,自由呼吸花果弥漫的空气。放牛时经常会有意外收获。比如,夏天,青青河边草地,坡上可以挖洞里的螃蟹,下河能抓小鱼。
割牛草要从年头贯穿到年尾,它是个体力活,也是个趣味活,还是个技术活。技术要领有三:磨刀、起早、占地。
磨刀不误砍柴工。刀不快,就出不了活。当月光映着已被磨成月芽状的磨刀石,往磨石上浇一点水,来来回回地磨砺,看着刀刃渐渐亮起来,用草叶在刀刃上“走一走”,直到刃能断发的程度,就算大功告成。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只有早起,才能获得就近的草资源,起晚了,近的山坡就被割光了。迟来的,就只有到更远处去寻找。有的时候,要到几里外才能找到一片青绿。
占到地盘心不慌。发现了一片青绿后,得马上在草地上割出一圈“外围”,就像在一座无人岛上插上了第一面旗帜,这才算是划归自己的领地了。后来者见草地已被“圈”起,就另寻他处去了。
割满了一背篓,一群孩子像凯旋的士兵,向着牛栏房归去。看着老牛偎在老树下细吞慢咽,天边的彩霞落在它的背上,晚风里掠过归巢的燕影,是童年里最为惬意的时刻,那种成就感难以言喻。
童年时代养育我的田园牧歌,像老牛反刍一般令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