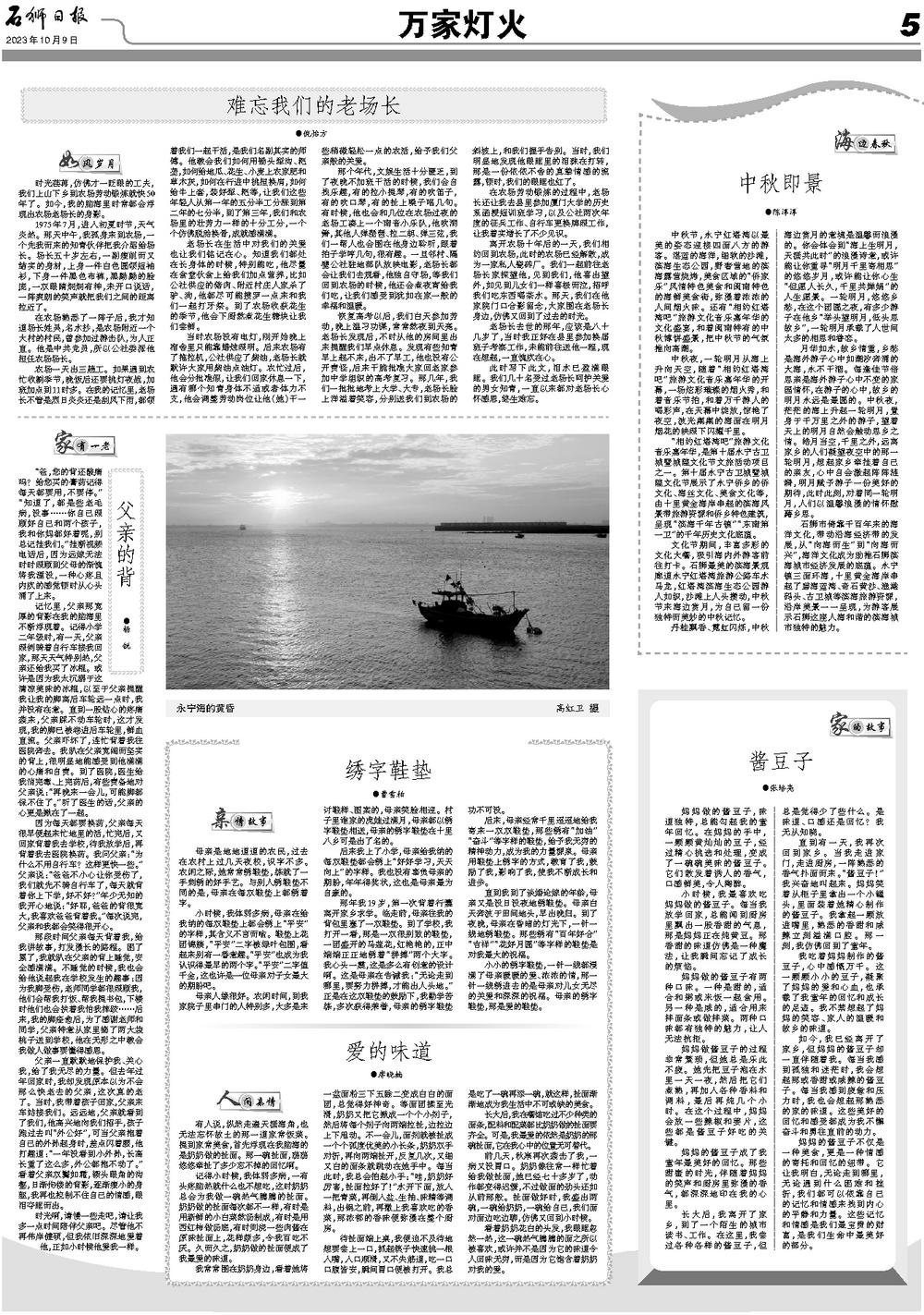●倪怡方
时光荏苒,仿佛才一眨眼的工夫,我们上山下乡到农场劳动锻炼就快50年了。如今,我的脑海里时常都会浮现出农场老场长的身影。
1975年7月,进入初夏时节,天气炎热。那天中午,我孤身来到农场,一个先我而来的知青伙伴把我介绍给场长。场长五十岁左右,一副瘦削而又结实的身材,上身一件白色圆领短袖衫,下身一件黑色布裤,黑黝黝的脸庞,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未开口说话,一阵爽朗的笑声就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在农场熟悉了一阵子后,我才知道场长姓吴,名水抄,是农场附近一个大村的村民,曾参加过游击队,为人正直。他是中共党员,所以公社委派他担任农场场长。
农场一天出三趟工。如果遇到农忙收割季节,晚饭后还要挑灯夜战,加班加点到11时多。在我的记忆里,老场长不管是烈日炎炎还是刮风下雨,都领着我们一起干活,是我们名副其实的师傅。他教会我们如何用锄头犁沟、耙垄,如何给地瓜、花生、小麦上农家肥和草木灰,如何在行进中挑担换肩,如何给牛上套,装好犁、耙等,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从第一年的五分半工分涨到第二年的七分半,到了第三年,我们和农场里的壮劳力一样的十分工分,一个个仿佛脱胎换骨,成就感满满。
老场长在生活中对我们的关爱也让我们铭记在心。知道我们都处在长身体的时候,特别能吃,他尽量在食堂伙食上给我们加点营养,比如公社供应的猪肉、附近村庄人家杀了驴、狗,他都尽可能搜罗一点来和我们一起打牙祭。到了农场收获花生的季节,他会下厨熬煮花生糖块让我们尝鲜。
当时农场没有电灯,刚开始晚上宿舍里只能靠蜡烛照明。后来农场有了拖拉机,公社供应了柴油,老场长就默许大家用柴油点油灯。农忙过后,他会分批准假,让我们回家休息一下,遇有哪个知青身体不适或者体力不支,他会调整劳动岗位让他(她)干一些稍微轻松一点的农活,给予我们父亲般的关爱。
那个年代,文娱生活十分匮乏,到了夜晚不加班干活的时候,我们会自找乐趣,有的拉小提琴,有的吹笛子,有的吹口琴,有的扯上嗓子唱几句。有时候,他也会和几位在农场过夜的老场工凑上一个南音小乐队,他吹洞箫,其他人弹琵琶、拉二胡、弹三弦,我们一帮人也会围在他身边聆听,跟着拍子学哼几句,很有趣。一旦邻村、隔壁公社驻地部队放映电影,老场长都会让我们去观看,他独自守场,等我们回到农场的时候,他还会煮夜宵给我们吃,让我们感受到犹如在家一般的幸福和温暖。
恢复高考以后,我们白天参加劳动,晚上温习功课,常常熬夜到天亮。老场长发现后,不时从他的房间里出来提醒我们早点休息。发现有些知青早上起不来,出不了早工,他也没有公开责怪,后来干脆批准大家回老家参加中学组织的高考复习。那几年,我们一批批地考上大学、大专,老场长脸上洋溢着笑容,分别送我们到农场的斜坡上,和我们握手告别。当时,我们明显地发现他眼眶里的泪珠在打转,那是一份依依不舍的真挚情感的流露,顿时,我们的眼眶也红了。
在农场劳动锻炼的过程中,老场长还让我去县里参加厦门大学的历史系函授短训班学习,以及公社两次年度的征兵工作、自行车更换牌照工作,让我着实增长了不少见识。
离开农场十年后的一天,我们相约回到农场,此时的农场已经解散,成为一家私人瓷砖厂。我们一起前往老场长家探望他,见到我们,他喜出望外,如见到儿女们一样喜极而泣,招呼我们吃东西喝茶水。那天,我们在他家院门口合影留念,大家围在老场长身边,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时光。
老场长去世的那年,应该是八十几岁了,当时我正好在县里参加换届班子考察工作,未能前往送他一程,现在想起,一直愧疚在心。
此时写下此文,泪水已盈满眼眶。我们几十名受过老场长呵护关爱的男女知青,一直以来都对老场长心怀感恩,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