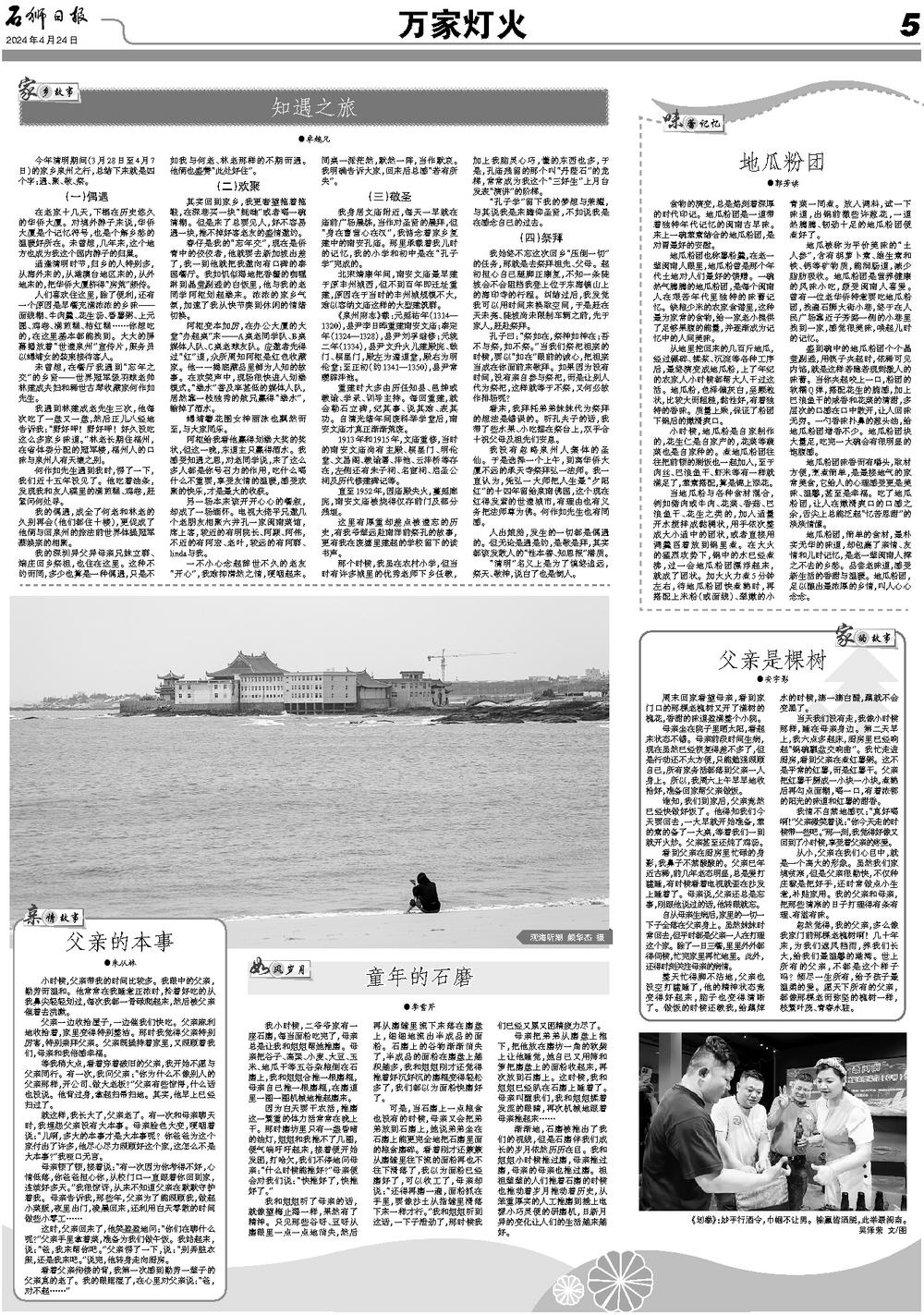●卓越兄
今年清明期间(3月28日至4月7日)的家乡泉州之行,总结下来就是四个字:遇、聚、敬、祭。
(一)偶遇
在老家十几天,下榻在历史悠久的华侨大厦。对境外游子来说,华侨大厦是个记忆符号,也是个解乡愁的温暖好所在。未曾想,几年来,这个地方也成为我这个国内游子的归巢。
适逢清明时节,归乡的人特别多,从海外来的,从港澳台地区来的,从外地来的,把华侨大厦挤得“房荒”频传。
人们喜欢住这里,除了便利,还有一个原因是早餐充满浓浓的乡味——面线糊、牛肉羹、花生汤、番薯粥、上元圆、鸡卷、满煎糕、桔红糕……你想吃的,在这里基本都能找到。大大的屏幕播放着“世遗泉州”宣传片,服务员以蟳埔女的装束接待客人。
未曾想,在餐厅我遇到“忘年之交”的乡贤——世界冠军级羽球老帅林建成夫妇和稀世古琴收藏家何作如先生。
我遇到林建成老先生三次,他每次吃了一盘又一盘,然后正儿八经地告诉我:“野好呷!野好呷!好久没吃这么多家乡味道。”林老长期住福州,在省体委分配的冠军楼,福州人的口味与泉州人有天壤之别。
何作如先生遇到我时,愣了一下,我们近十五年没见了。他吃着油条,发现我和友人碟里的满煎糕、鸡卷,赶紧问何处寻。
我的偶遇,成全了何老和林老的久别再会(他们都住十楼),更促成了他俩与回泉州的旅法前世界体操冠军蔡焕宗的相聚。
我的深圳异父异母亲兄妹立群、端庄回乡祭祖,也住在这里。这种不约而同,多少也算是一种偶遇,只是不如我与何老、林老那样的不期而遇。他俩也盛赞“此处好住”。
(二)欢聚
其实回到家乡,我更奢望拖着拖鞋,在深巷买一块“蚝哋”或者喝一碗清糊。但是来了总要见人,好不容易遇一块,推不掉好客老友的盛情邀约。
春仔是我的“忘年交”,现在是侨青中的佼佼者,他就要去新加坡出差了,我一到他就把我邀向有口碑的泰国餐厅。我如饥似渴地把香蟹的咖喱淋到晶莹剔透的白饭里,他与我的老同学阿枢划起拳来。浓浓的家乡气氛,加速了我从快节奏到休闲的情绪切换。
阿枢变本加厉,在办公大厦的大堂“办起桌”来——A桌老同学队、B桌媒体人队、C桌老球友队。应邀者先得过“红”道,众所周知阿枢是红色收藏家。他一一揭底藏品里鲜为人知的故事。在欢笑声中,现场很快进入划拳模式。“拳水”普及率甚低的媒体人队,居然靠一枝独秀的航兄赢得“拳水”,输掉了酒水。
蟳埔簪花围女神丽泳也飘然而至,与大家同乐。
阿枢给我看他赢得划拳大奖的奖状,但这一晚,东道主只赢得酒水。我感受知遇之恩,对老同学说,来了这么多人都是你号召力的作用,吃什么喝什么不重要,享受友情的温暖,感受欢聚的快乐,才是最大的收获。
另一场本来该开开心心的餐叙,却成了一场缅怀。电视大佬平兄邀几个老朋友相聚六井孔一家闽南菜馆,席上客,较近的有明院长、阿颖、阿伟,不近的有阿宏、老叶,较远的有阿群、linda与我。
一不小心念起辞世不久的老友“开心”,我难抑潸然之情,哽咽起来。同桌一派茫然,默然一阵,当作默哀。我明确告诉大家,回来后总感“若有所失”。
(三)敬圣
我身居文庙附近,每天一早就在庙前广场晨练,当作对圣贤的晨拜,但“身在曹营心在汉”,我惦念着家乡复建中的南安孔庙。那里承载着我儿时的记忆,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孔子学”完成的。
北宋靖康年间,南安文庙最早建于原丰州城西,但不到百年即迁址重建,原因在于当时的丰州城规模不大,难以容纳文庙这样的大型建筑群。
《泉州府志》载:元延祐年(1314—1320),县尹李日晔重建南安文庙;泰定年(1324—1328),县尹刘孚继修;元统二年(1334),县尹文升火儿建殿庑、戟门、棂星门,殿左为遵道堂,殿右为明伦堂;至正初(约1341—1350),县尹常瓒辟泮池。
重建时大多由历任知县、邑绅或教谕、学录、训导主持。每回重建,就会勒石立碑,纪其事、说其难、表其功。自清光绪年间废科举学堂后,南安文庙才真正渐渐荒废。
1913年和1915年,文庙重修,当时的南安文庙尚有主殿、棂星门、明伦堂、文昌阁、教谕署、泮池、云泮桥等存在,左侧还有朱子祠、名宦祠、启圣公祠及历代修建碑记等。
直至1952年,因庙殿失火,蔓延廊庑,南安文庙被烧得仅存前门及部分残垣。
这里有厚重却差点被遗忘的历史,有我爷辈远赴南洋前祭孔的故事,更有我在废墟里建起的学校留下的读书声。
那个时候,我虽在农村小学,但当时有许多城里的优秀老师下乡任教,加上我脑灵心巧,懂的东西也多,于是,孔庙残留的那个叫“丹陛石”的龙梯,常常成为我这个“三好生”上月台发表“演讲”的阶梯。
“孔子学”留下我的梦想与荣耀,与其说我是来瞻仰圣贤,不如说我是在感念自己的过去。
(四)祭拜
我始终不忘这次回乡“压倒一切”的任务,那就是去祭拜祖先、父母。起初担心自己腿脚正康复,不知一条陡坡会不会阻挡我登上位于东海镇山上的海印寺的行程。纠结过后,我发觉我可以用时间来换取空间,于是赶在天未亮、陡坡尚未限制车辆之前,先于家人,赶赴祭拜。
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当我们祭祀祖宗的时候,要以“如在”眼前的诚心,把祖宗当成在你面前来敬拜。如果因为没有时间,没有亲自参与祭祀,而是让别人代为祭祀,这样就等于不祭,又何必故作排场呢?
看来,我拜托弟弟妹妹代为祭拜的想法是错误的。听孔夫子的话,我带了些水果、小吃摆在祭台上,双手合十祝父母及祖先们安息。
我没有忽略泉州人集体的圣仙。于是选择一个上午,到离华侨大厦不远的承天寺祭拜弘一法师。我一直认为,凭弘一大师把人生最“夕阳红”的十四年留给泉南佛国,这个现在红得发紫的世遗城市,有理由也有义务把法师尊为佛。何作如先生也有同感。
人出娘胎,发生的一切都是偶遇的。但无论是遇是约,是敬是拜,其实都该发散人的“性本善、知恩报”潜质。
“清明”名义上是为了慎终追远,祭天、敬神,说白了也是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