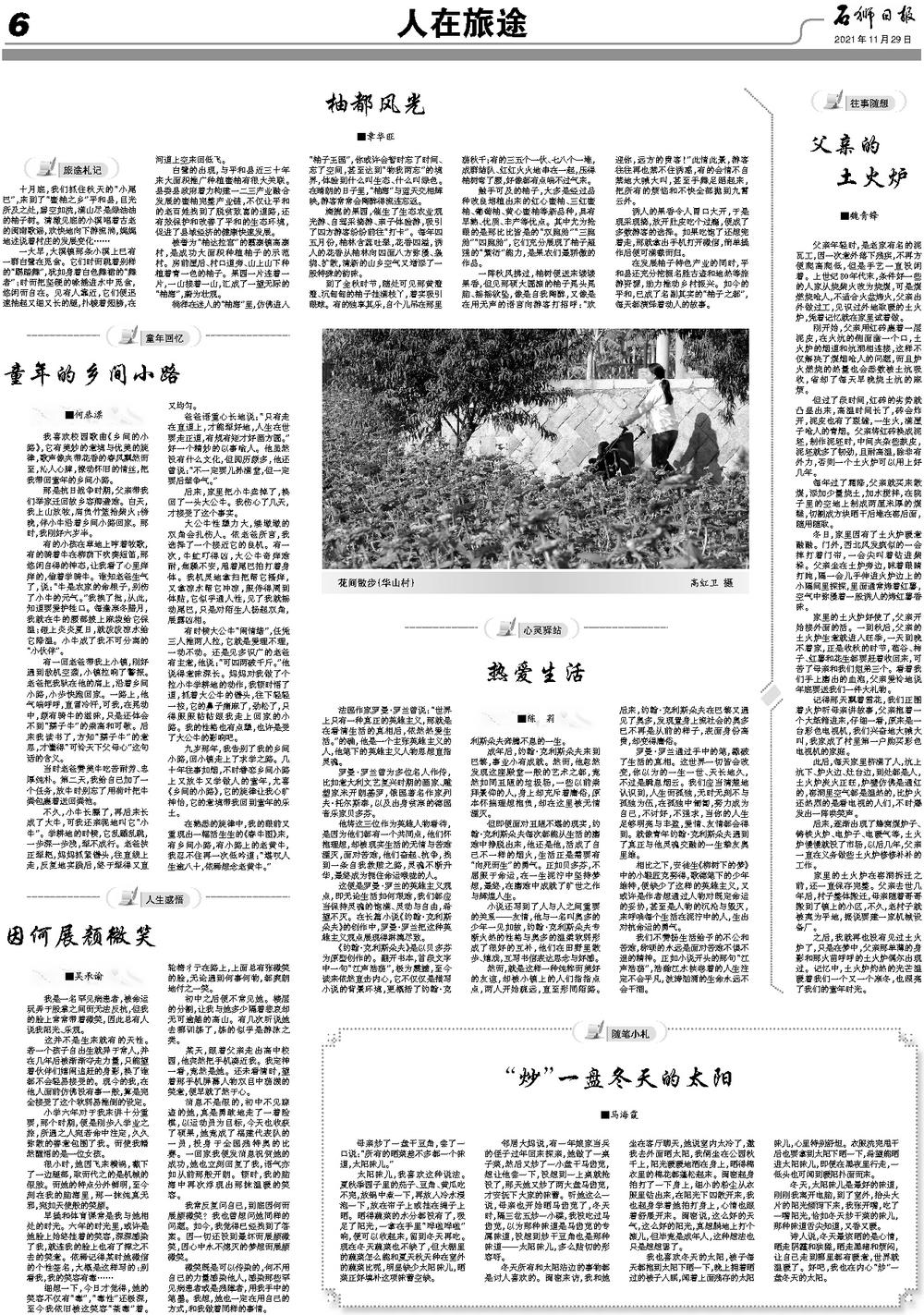父亲年轻时,是老家有名的泥瓦工,因一次意外落下残疾,不再方便爬高爬低,但是手艺一直没闲着。上世纪80年代末,条件好一些的人家从烧柴火改为烧煤,可是煤燃烧呛人,不适合火盆烤火,父亲出外做过工,见识过外地取暖的土火炉,凭着记忆就在家里试着做。
刚开始,父亲用红砖裹着一层泥皮,在火炕的侧面凿一个口,土火炉的烟道和炕洞相连接,这样不仅解决了煤烟呛人的问题,而且炉火燃烧的热量也会悉数被土炕吸收,省却了每天早晚烧土炕的麻烦。
但过了段时间,红砖的劣势就凸显出来,高温时间长了,砖会炸开,泥皮也有了裂缝,一生火,满屋子呛人的青烟。父亲将红砖换成泥坯,制作泥坯时,中间夹杂些麸皮,泥坯就多了韧劲,且耐高温,除非有外力,否则一个土火炉可以用上好几年。
每年过了霜降,父亲就买来散煤,添加少量烧土,加水搅拌,在院子里的空地上制成两厘米厚的煤糕,切割成方块晒干后堆在窑后面,随用随取。
冬日,家里因有了土火炉暖意融融。门外,西北风发疯似的一会摔打着门帘,一会尖叫着钻进柴垛。父亲坐在土炉旁边,眯着眼睛打盹,隔一会儿手伸进火炉边上的小隔间里探探,里面通常烤着红薯,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诱人的烤红薯香味。
家里的土火炉好使了,父亲开始接外面的活。一到秋后,父亲的土火炉生意就进入旺季,一天到晚不着家,正是收秋的时节,苞谷、柿子、红薯和花生都要赶着收回来,可苦了母亲和我们姐弟三个。看着我们手上磨出的血泡,父亲爱怜地说年底要送我们一件大礼物。
记得那天飘着雪花,我们正围着火炉听母亲讲故事,父亲抱着一个大纸箱进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台彩色电视机,我们兴奋地大喊大叫,我家成了村里第一户购买彩色电视机的家庭。
此后,每天家里挤满了人,炕上炕下、炉火边、灶台边,到处都是人,土火炉炭火正旺,炉壁仿佛是通红的,窑洞里空气都是温热的,比炉火还热烈的是看电视的人们,不时爆发出一阵哄笑声。
后来,逐渐出现了蜂窝煤炉子、铸铁火炉、电炉子、电暖气等,土火炉慢慢就没了市场,以后几年,父亲一直在义务做些土火炉修修补补的工作。
家里的土火炉在窑洞拆迁之前,还一直保存完整。父亲去世几年后,村子整体搬迁,母亲随着哥哥搬到了镇上的小区,不久,老村子就被夷为平地,据说要建一家机械设备厂。
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土火炉了,只是在梦中,父亲那单薄的身影和那火苗呼呼的土火炉偶尔出现过。记忆中,土火炉灼热的光芒温暖着我们一个又一个寒冬,也照亮了我们的童年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