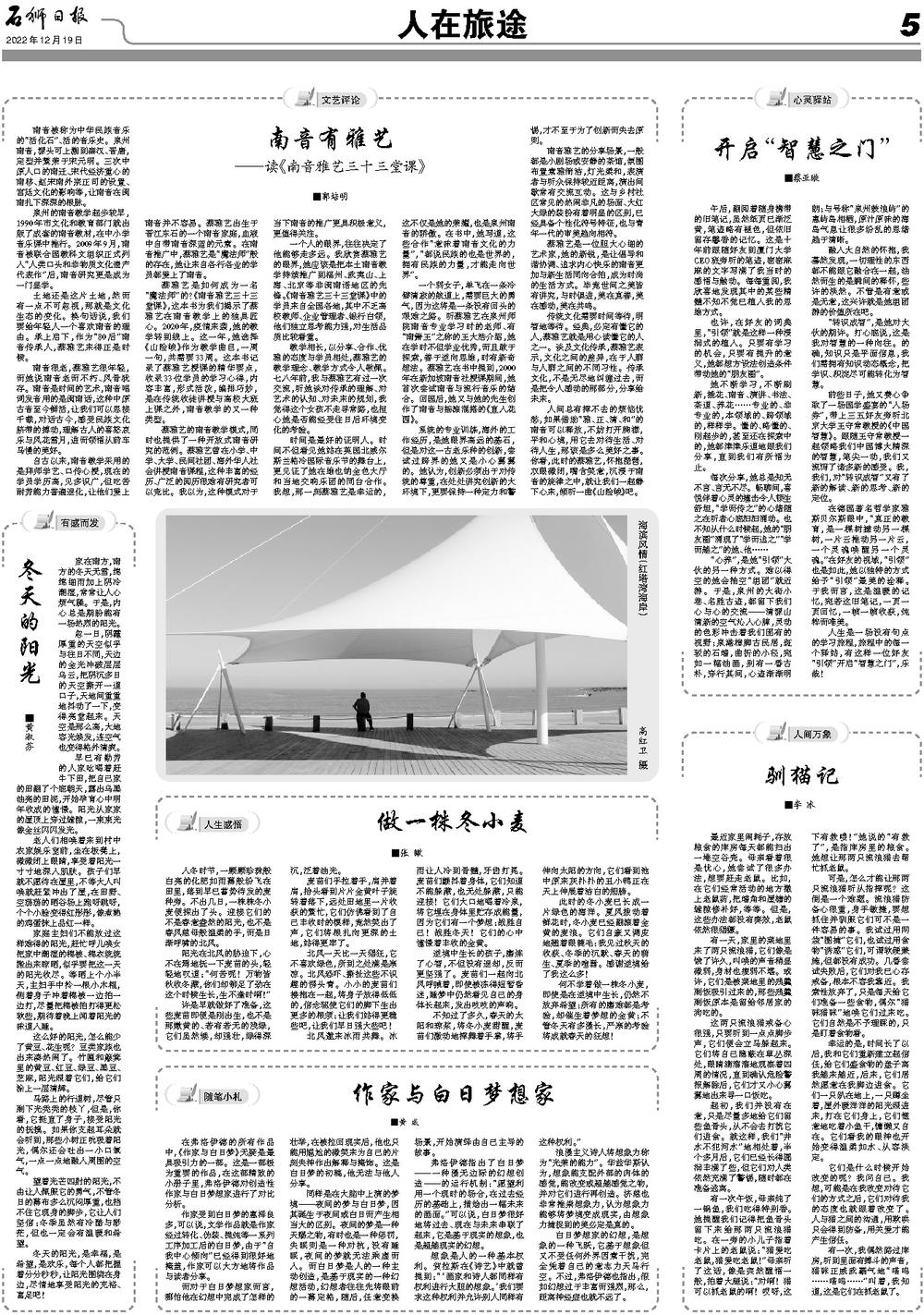■郭培明
南音被称为中华民族音乐的“活化石”、活的音乐史。泉州南音,源头可上溯到秦汉、晋唐,定型并繁荣于宋元明。三次中原人口的南迁、宋代经济重心的南移、赵宋南外宗正司的设置、宫廷文化的影响等,让南音在闽南扎下深深的根脉。
泉州的南音教学起步较早,1990年市文化和教育部门就出版了成套的南音教材,在中小学音乐课中推行。2009年9月,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后,南音研究更是成为一门显学。
土地还是这片土地,然而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文化生态的变化。换句话说,我们要给年轻人一个喜欢南音的理由。承上启下,作为“80后”南音传承人,蔡雅艺来得正是时候。
南音很老,蔡雅艺很年轻,而她说南音老而不朽、风骨犹存。南音是时间的艺术,南音唱词发音用的是闽南话,这种中原古音至今鲜活,让我们可以思接千载,对话古今,感受民族文化脐带的搏动,理解古人的喜怒哀乐与风花雪月,进而领悟从前车马慢的美好。
自古以来,南音教学采用的是拜师学艺、口传心授,现在的学员学历高,见多识广,但吃苦耐劳能力普遍退化,让他们爱上南音并不容易。蔡雅艺出生于晋江东石的一个南音家庭,血液中自带南音深蓝的元素。在南音推广中,蔡雅艺是“魔法师”般的存在,她让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都爱上了南音。
蔡雅艺是如何成为一名“魔法师”的?《南音雅艺三十三堂课》,这本书为我们揭示了蔡雅艺在南音教学上的独具匠心。2020年,疫情来袭,她的教学转到线上。这一年,她选择《山险峻》作为教学曲目,一周一句,共需要33周。这本书记录了蔡雅艺授课的精华要点,收录33位学员的学习心得,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编排巧妙,是在传统收徒讲授与高校大班上课之外,南音教学的又一种类型。
蔡雅艺的南音教学模式,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开放式南音研究的范例。蔡雅艺曾在小学、中学、大学、民间社团、海外华人社会讲授南音课程,这种丰富的经历、广泛的阅历很难有研究者可以竞比。我以为,这种模式对于当下南音的推广更具积极意义,更值得关注。
一个人的眼界,往往决定了他能够走多远。我欣赏蔡雅艺的眼界,她应该是把本土南音教学持续推广到福州、武夷山、上海、北京等非闽南语地区的先锋。《南音雅艺三十三堂课》中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其中不乏高校教师、企业管理者、银行白领,他们独立思考能力强,对生活品质比较看重。
教学相长,以分享、合作、优雅的态度与学员相处,蔡雅艺的教学理念、教学方式令人敬佩。七八年前,我与蔡雅艺有过一次交流,听她谈对传承的理解、对艺术的认知、对未来的规划,我觉得这个女孩不走寻常路,也担心她是否能经受住日后环境变化的考验。
时间是最好的证明人。时间不但看见她站在英国北威尔斯兰格冷国际音乐节的舞台上,更见证了她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和当地交响乐团的同台合作。我想,那一刻蔡雅艺是幸运的,这不仅是她的荣耀,也是泉州南音的骄傲。在书中,她写道,这些合作“意味着南音文化的力量”,“都说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拥有民族的力量,才能走向世界”。
一个弱女子,单飞在一条冷僻清寂的航道上,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这将是一条没有回头的艰难之路。听蔡雅艺在泉州师院南音专业学习时的老师、有“南箫王”之称的王大浩介绍,她在学时不但学业优秀,而且敢于探索,善于逆向思维,时有新奇想法。蔡雅艺在书中提到,2000年在新加坡南音社授课期间,她首次尝试南音与流行音乐的结合。回国后,她又与她的先生创作了南音与摇滚混搭的《直入花园》。
系统的专业训练,海外的工作经历,是她眼界高远的基石,但是对这一古老乐种的创新,尝试过跨界的她又是小心翼翼的。她认为,创新必须出于对传统的尊重,在处处讲究创新的大环境下,更要保持一种定力和警惕,才不至于为了创新而失去原则。
南音雅艺的分享场景,一般都是小剧场或安静的茶馆,氛围布置素雅简洁,灯光柔和,表演者与听众保持较近距离,演出间歇常有交流互动。这与乡村社区常见的热闹非凡的场面、大红大绿的装扮有着明显的区别,已经具备个性化符号特征,也与青年一代的审美趋向相符。
蔡雅艺是一位胆大心细的艺术家,她的新锐,是让倡导和谐协调、追求内心快乐的南音更加与新生活同向合拍,成为时尚的生活方式。毕竟世间之美皆有讲究,与时俱进,美在真善,美在感动,美在共鸣。
传统文化需要时间等待,明智地等待。经典,必定有懂它的人,蔡雅艺就是用心读懂它的人之一。谈及文化传承,蔡雅艺表示,文化之间的差异,在于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不同习性。传承文化,不是无尽地纠缠过去,而是把令人感动的那部分,分享给未来。
人间总有挥不去的烦恼忧愁,如果借助“雅、正、清、和”的南音可以释放,不妨打开胸襟,平和心境,用它去对待生活、对待人生,那该是多么美好之事。你看,此时的蔡雅艺,怀抱琵琶,双眼微闭,嘴含笑意,沉浸于南音的旋律之中,就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倾听一曲《山险峻》吧。